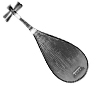古代诗歌喜用数字,有个从少到多,从一般选用到追求神奇效果的使用过程。大体上说,数字入诗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至南北朝,鼎盛于唐。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出现了反复使用数字的诗。描写青年男子思慕爱人的《王风·采葛》,一章比一章夸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语意递增,情感深化,多次运用夸张构筑了深远的意境,使人易诵、乐背,历久不忘,此诗开创了巧用数字之先河。委婉语是先秦著作中常见的重要修辞格,它也反映在《诗经》含数字的诗中,如《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以“百岁”代死后,表达了丧偶的少妇深切思念亡夫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但总的说来,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的诗人尚未能体会到奇妙多变的数字对开拓诗的意境、提高诗的思想性及艺术表现力有重要作用,加之受量词出现晚的制约,数字的自觉选用并不多。
两汉至南北朝,以数字见新意的诗多了起来。这与诗人注重运用数字有关,也与量词的增多有涉。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量词发展,名量词分工细密,数量增加,超过了前代,而动量词也由新兴渐入成熟。动量词具有一定的形象性,能增强诗歌的感染力。于是,在这一漫长时代中,无论是民歌,还是文人诗作,数词和量词的使用逐渐多了起来,说它们以数为主,以量以辅,融合渗透,合二为一,实不为过。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末段写罗敷夸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不妨说,罗敷有意凭借数量词夸赞了夫婿风华正茂,官位一升再升。夸张铺陈的目的是夸夫不同凡响,才干超群,是数量词诠释了“殊”字的丰富内容,终于灭掉了“使君”的威风,使他溜走了事。我们又自然想到被明代王世贞称之为“长诗之圣”的《孔雀东南飞》,其诗首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托物起兴,渲染了全诗的依恋不舍、缠绵凄凉的悲剧气氛,起到了统摄全诗,导引下文的作用。紧接着,通过刘兰芝向丈夫的诉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夫,心中常苦悲。”由起兴转入铺陈,句句用数,刻画了刘兰芝是位善于纺织裁缝,明诗书达礼乐的妇女形象。曹操的代表作《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又是用饱含血泪的数字真实形象地再现了汉末的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现实。可见,数字在要求形象、精炼的诗句中举足轻重,是其他词类的词不可取代的。
唐代诗人偏爱数字,甚至达到了离开数字便无法成诗的地步。特别是近体诗成熟之后,许多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刘禹锡、孟郊、柳宗元、张祜、李贺、许浑、杜牧、李商隐等无不是活用数词的高手。为何有唐诗人偏爱数字呢?我们认为这是诗歌本身的需要,更是数词有独特艺术价值造成的。它使数字与修辞水乳交融,互相映衬,共同开掘深化了诗意,使诗作本身产生了超出诗人构思时的艺术感染力。
一、连用性
不难发现,许多唐诗往往会句句用数,或是大多数诗句巧用数字。不少诗人在连续使用数字时表现出的创意、新奇,使数字入诗既能描绘千差万别的景色,又能淋漓尽致地抒发喜怒哀乐的情怀。数字分工不同,且又浑然一体,诗意一以贯之,情感一气呵成。
张祜的《宫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首直叙其事,直写其情的宫怨诗,只二十个字,却句句有数字。用“三千里”,写宫女离家之远(“故国”是故乡之意,因这首诗是仄起仄收式,故首句第二个字只可用入声字“国”,不可用平声字“乡”)妙龄离乡背井,终生难见亲人,此句点明地点。“二十年”写入宫之久,已人到中年,这句写时间。首联用表空间和时间的数量词极力渲染了地远时久的悲痛氛围,宫女的可怜可悲如在眼前。但诗人的笔触于此未止,又用“一声”、“双泪”将宫女无法控制的泪水直洒寻欢作乐的君王面前,这两个数量词的份量和揭露深度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数量词成了全诗的灵魂。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杜甫绝句的代表作。“两个”是点,“一行”为线,“千秋”含史,“万里”写今,景色优美,情绪欢快。若将四个数量词删掉或代之他词,则难免使原诗黯然失色。何也?因为看似平直的数量词隐含着诗人复杂的内心思想活动。尤其是“万里”,点明了安史之乱已平,船只来自万里之遥的东吴,这正是奠定该诗欢快基调的所在。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四句中三句用数,选用“千里”、“两岸”、“万重”,紧扣了一个“快”字——诗人心中畅快,又写船只飞快。以数抒情,实现了诗人与读者在情感上的直接交流。应该说,数量词是使该诗“行之久远”的重要因素。
至于柳宗元的《江雪》,韵脚虽押入声韵,但即使少年,也能背诵如流,大概与嵌入数量词有很大关系:诗人用“千山”、“万径”作为宏观远景,突出了“孤舟”“独钓”的特写镜头(“孤”“独”在古诗中也属数目字一类),用心品味,还有比数量词勾勒的这一画面更静谧、洁白的吗?刘叉的《偶书》:“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正是靠这把寒光熠烁的“万古刀”折射出诗人侠肝义胆的强烈个性,才使这首抒怀诗也能流传万古。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诗人用几个数量词将日沉月升的大自然美景作了出神入化的描写,给后人以美的享受。
二、可比性
世间人、事、物都有对立面,均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中,所以汉语中才会有那么多鲜明深刻的反义词。诗歌中恰当地运用数字也会造成强烈的反差,揭示人、事或社会的本质,引人深思,使人难忘。数字的可比性,在唐诗中屡见不鲜。
刘禹锡的《台城》先写六朝皇帝荒淫奢侈,而最甚者当属营造了结绮、临春、望仙三座楼阁的陈后主:“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次写当年景象繁华的“万户千门”如今变为“野草”,令人怵目惊心。结尾以诗的语言用听觉形象挑明了陈后主亡国的原因——“只缘一曲后庭花”,便毁掉了豪华气派的“万户千门”。“一曲”与前面的三个数量词构成强烈对比,这一巨变,不正是历史上无数惊人相似的缩影吗?
读白居易的诗,常有无数不成诗的感觉。很多诗通过数字的两两对比,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感染力。“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上阳白发人》)。十六岁豆寇年华,六十岁白发垂暮,将十六岁颠倒,时间跨度为四十四年,涵盖了一个靓丽女子的整个青春年华,最宝贵的时光竟断送在深宫中,读至此,能不震撼读者的心灵吗?实是作者有感而发的血泪控诉!“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卖炭翁》)。卖炭翁一心希望卖个好价钱,换来的却是宫中多余的无用之物,夺走的是他的活命钱。数量词的对比,引发了读者的深思和愤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长恨歌》),杨贵妃的美貌、风度、多情、能歌善舞都融入对比的数字之中了。诗人《买花》中的结尾应是唐诗中运用对比手法的优秀之作:“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花掉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贫富不均,社会矛盾的尖锐,通过田舍翁的感叹,确切地说,是诗人的无限感慨,从字里行间里流露出来,从而实践了作者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三、替代性
数词不同于代词,数词也与修辞中的借代大相径庭。但我们从不少唐诗中,却惊奇地看到数字入诗竟然有替代人的作用,且和修辞中的拟人、拟物或比喻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昌龄的《采莲曲二首(其二)》,数字“两”用得极活甚妙:“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采莲少女身着荷叶一样的绿罗裙,置身田田荷叶中,诗人先描写了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美境,令人惊叹的是第二句的“两”字,它描绘了荷花似青春少女那样鲜艳娇美,而少女的脸庞又如荷花那般红润艳丽,人花难辨,融为一体。一个“两”字既替代了荷花,又暗指了少女,拟人、拟物糅合交错,使整首诗充满了青春活力。
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也是妙用“两”字、独具匠心的数字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人先用“众”、“孤”两个数字极力渲染了一个静的世界,仿佛世上只剩下诗人了,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和寂寞。后两句赋予了敬亭山以生命和感情。“只”虽不是数字,但此处含有“一”的意思。只有这座山脉脉含情地望着作者,诗人喜爱大山,大山钟情诗人,这拟人手法的高超运用,是因为选择了具有替代作用的数字“两”的缘故。
诗仙的另一首名诗《月下独酌四首(其一)》也是诗人一人,独酌无亲,冷清寂寞,突发奇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连同明月、人影化成三人,与上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以拟人辞格,巧用数量词将冷清的场面写活了。
四、夸饰性
赵克勤先生认为,“夸张”是故意渲染以唤起注意,而诗歌是最需要“渲染”的一种文学体裁,数字的灵活运用自然成了承担这一要求的载体。数字可以突破现实生活的“形似”而创造出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寓情理之中的“神似”的境界,令人信服。运用数字,只要“夸而有节,饰而不诬”〔1〕(《夸饰》),便可成“百”上“千”地夸张,以求达到艺术的真实。这便是“辞虽已甚,其义无害。”〔1〕(《夸饰》)唐代诗人充分利用数字的艺术作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千古传诵的诗篇,并成为后人借鉴的典范。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一个“挂”字,似无形的巨手,将硕大的白练高高挑于山前。“飞流直下三千尺”,瀑布之猛之高之响,惊心动魄,壮观至极。最后,又用数量词再次将夸张推向极致,这飞腾的瀑布莫非是银河从九天凌空而落?这首深深烙印在读者心田的山水诗,数字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则以数字重重地凝聚了一个“愁”字:“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染白霜。”诗人有以山写愁的,有以水喻愁的,而李白的愁无尽无休,如何来写?他别出心裁,竟以“三千丈”之长的白发喻愁,极言愁之深重,他用艺术的真实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把诗的基础和灵魂——感情,做了最大的渲染,自然而然引起了读者的深刻同情——为才华横溢的诗人长期受压抑排挤而愤愤不平!
诗仙之名已含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李白善用夸张又是构成这种色彩的主要成分。特别是极能表现他个性的咏酒诗,不少诗中借数量词塑造了诗人的高大形象,抒豪情,展壮志,痛快淋漓,其代表作当属脍炙人口的《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怀……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唐诗中善用数字夸张者众多,唐代之后常有人不解夸张的用意,而是用生活的真实去衡量艺术的真实,对唐人的数字夸张诗篇多有微辞。杜甫的《古柏行》,有“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两句,作者歌咏夔州诸葛亮庙的古柏树,以“四十围”极言其大,用“两千尺”极言其高,意在以古柏的高大象征孔明人格的伟大。如果机械地计算古柏的“四十围”和“二千尺”,讥讽杜甫写得不合情理,,这是不懂艺术的表现。可见,杜诗运用夸张,并没脱离树大树高的原有基础。正如王国维所言:“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2〕杜甫的诗句不正反映了诗人是理想家兼写实家吗?
五、对称性
近体诗在格律上的一大特点是讲究对仗,即中间两联一般要用对仗。对仗不仅使律诗的形式美观,雅俗共赏,而且在内容上又呼应渗透,使诗意更加深沉,是诗人刻意追求的重要辞格。选用数字嵌入对偶句中,在律诗中俯拾即是,作用非常。前面所举例诗,有不少是数字对偶句。以下诗篇,也十分典型。
被诗评家胡应麟在《诗薮》中誉为古今七律之冠的《登高》,首联和颔联极力描绘浓郁的秋日,铸成了千古流传的佳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而颈联中的数量词却是全诗的中流砥柱。全诗在谋篇、造句、炼字上,超凡奇特,尤以颈联为最。一些诗评家和注者已指出该联有八层意思:“万里”,地隔遥远;“悲秋”,时序凄凉;“作客”,羁留他乡;“常作客”,羁旅长久;“百年”,已至晚年;“多病”体弱难支;“登台”,遥望故土;“独登台”,没有亲朋。但对仗极工的八层意思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以“万里”统领全联,“百年”又带起全句。扩而大之,这两个极平常的数量词是全诗之总纲,所有句、词以它为核心精心选择、造句。诗人抓准了登高时自身最重要的两点:“万里”——远离故土;“百年”——人到暮年。正因如此,时值秋日,才有“悲秋”之感;客居他乡,才有“作客”之语,而以“常”字冠之,足见经常飘泊,使人自然想起“客舍似家家似寄”的诗句。这几层意思都是由“万里”而生,是对“万里”的有机补充。依此分析,“多病”、“独登台”也是紧紧围绕“百年”来写的。首联和颔联是客居他乡的秋景,尾联的“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是“百年”寓意的延伸,如果说杜甫的《登高》为古今七律第一,那么,对仗的数量词则是夺冠的基石。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其诗气势磅礴,读之如身临其境,胸襟顿开。结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典型的流水对,语言朴实,却富于只有登高才可望远的哲理,而这一哲理又是靠表达远望和登高的数量词展现的。“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首联起句不凡,数量词相对,又与互文并用,使意境无限阔大。颔联转向特写:一夜山雨,百泉飞泻,景象秀美,令人神往。两联中四用数量词起到了视点由远及近,意境由宏大深远而清晰具体的奇特作用。常被人援引的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仅对句工整,而且两个数量词如一木顶千斤,使诗句神完气足。“千帆过”,写足气势;“万木春”,写够精神。
以上简述,剖析了古代诗歌中数字的独特艺术价值。说明了巧用数字有利于言志、抒情、绘景、状物,因此数字成为诗人笔下的常客,诗中的珍品,这便是众多含数字的古诗久传不衰的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0-01-03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济南:齐鲁书社,1982.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